

历史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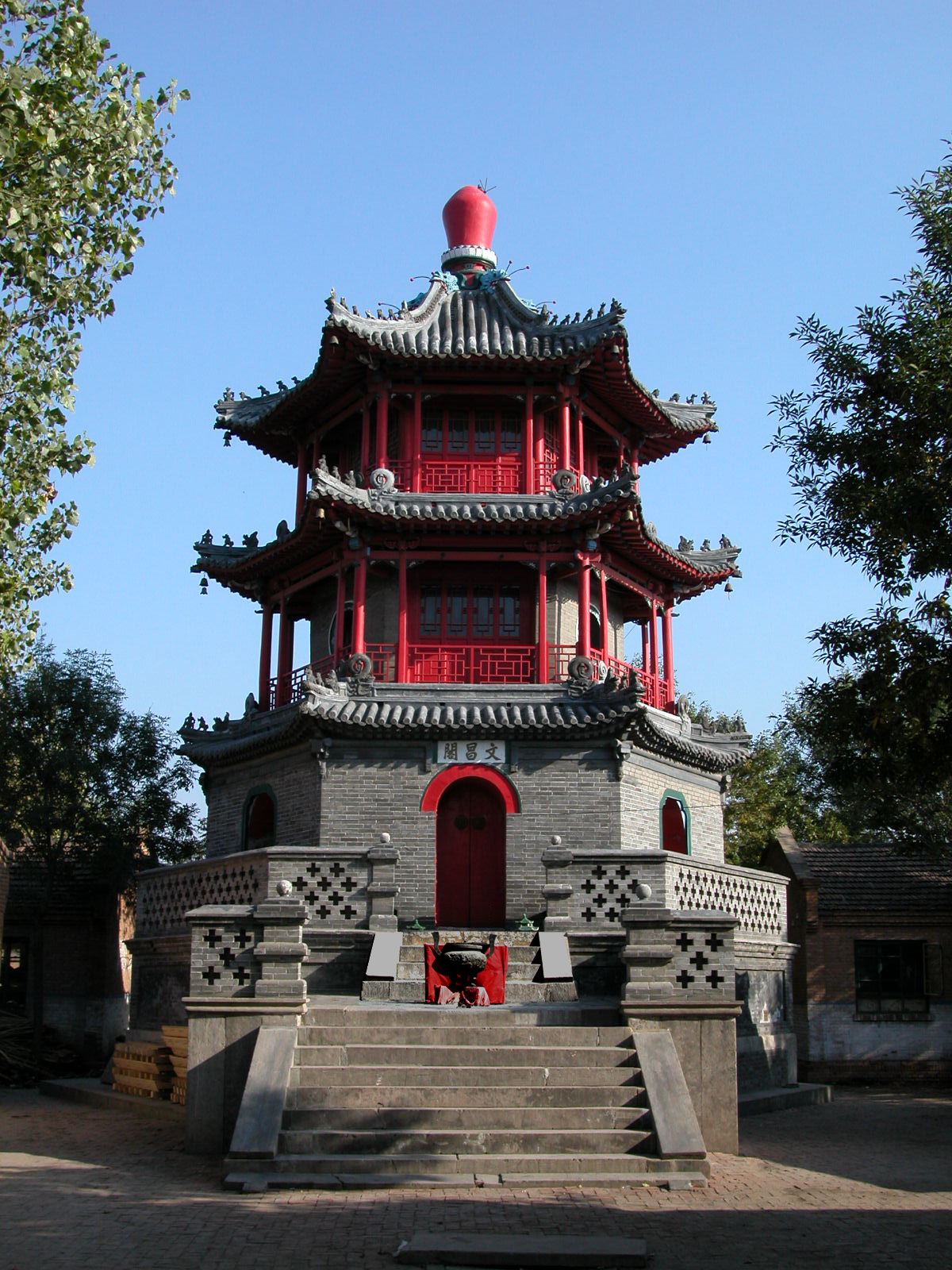
十一、过瘾
由于杨柳青是一个五方杂居之地,信仰佛道神鬼魔的人也各不相同,于是就出现很多祭祀仪式,最大众化的算是民间花会,它不但花样多,更需要许多的人参与,因此它就蜕变成为一项平民化的大型娱乐活动。据调查,旧时,杨柳青有70多道花会,其会头百分之百是私人,大多数是家庭为一个组织单位,或召集人,或聘请会把式的能人教授,或出资或募资,或置办行套,或组织比赛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瘾头儿。队员们也是百分百的业余参与者,他们白天各干各的活儿,夜晚汇集到各个会头家开始练习,唱的、跳的、闹得、喊的、笑的,进入自己的角色。五十年代,杨柳青搬运工会练习舞龙动作,最初置备不起正式的器械,只能把一个个挑土的土筐用绳子连起来作龙身。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跨队练习,比如舞龙、高跷、少林功夫,甚至是香塔的一名吹鼓手,他可以在任何一个队里玩儿,但是有一样儿,在正式表演时,一定要确定一个表演队或一个表演角色,以免误事。不然的话,即使是能能人,但不着调,那就要落个“没正形”的坏名声。这样的坏名声往往会落到有能能人身上。我的邻居卞小二儿,那小伙子长得帅气,脑瓜子灵,只要他上手,就没有学不会的。高跷、头棒、武松,他看别人耍完,绑上腿子耍起来,不逊色于老师傅。耍龙灯,辗、转、腾、挪没有不会的。吹奏乐之类的,拿起来也能吹几下。他这也叫过瘾,可就是对什么都没长性,不能把瘾转变成长久坚持的精神。这种没正形的人让人靠不住,所以老师傅们也不指望他。
十二、画师请客(让大家给画提意见)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一点都不错,特别是耍手艺的。比如,木匠到了一块儿,见对方打的八仙桌四角有一角八字榫内角稍有偏差,马上说“老王可以,八仙桌子打得不错呀,这个榫子挺有特性的。”对方脸上立刻挂不住了,马上装笑说“行啊,老张不愧是师傅级的人物,听说你老打的柜子没注意就地的高低呀!”他们就是这样以斗嘴的方式,互相吹捧,夹腔儿带棒,话里带刺儿,且暗地里互相把次得一文不值。有好事者,又互相传话,弄得互相谁也不想见谁,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他们还是师兄弟。文人也一样,叫文人相欺,文人到了一块儿,那还了得,你一句我一句,骂人不带脏字儿,损人不吐核儿。敦厚老实的人只有熋(nai)改的份儿,原因是不会接话,更不会看巧儿。可杨柳青有一个传下来的好文风——文人相亲,互相帮衬。老年画师们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过去,年画师们时不时聚在一起,或谈古说今,或点品年画样子,说话中肯,建议适当,丝毫没有侮辱对方的样子。有一次,一个年画师出了画样儿,挂在墙上,把大伙召集在一起,一边请大伙聚一聚吃点小菜儿,一边让大家对他这副画样儿掌掌眼,然后,这个一言,那个一语。这些言语对作画者来说也许对也许错,对的,他点头,记在心里,错的也点头或当耳旁风,或当下次作画的元素记在心里。”通过这样纠错再修改后而形成最后画稿将是非常棒的,这就是为什么杨柳青年画每出一幅都是精品的原因,与其说一张年画是一个画师的作品,倒不如说它是大家智慧的结晶。出画样者这样做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宣布这张年画的著作权,暗意是:这张年画是我创作的,以后不要仿造。不过无论是哪种意图,他们都是君子所为,摆在桌面上。现在的杨柳青文人或画家们真应该好好向前辈学习,努力学本领,历练胸怀,互相帮衬,只有具备这种精神,他们才会像杨柳青年画一样,走出天津,奔向全国,走向世界。
十三、老太太的画抵不过小孩
“家家善丹青,人人会点染”是描述清康嘉时期杨柳青年画鼎盛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在杨柳青三条街(河沿街、估衣街、席市大街)合起来不过三百米长的街面,有卖年画、制做年画及与之有关的刻版店、裱画店等二百来家。仅戴连增、齐健隆、王雕版、忠兴号几家大年画店就供养着画师、画工千余名。他们大量印制墨线版,分派给杨柳青镇南三十六村及邻近静海县的唐官屯以北大片农村的农民来加工年画,在这些农民画工中有很多老太太,她们心灵手巧,制作出很多精美传世的仕女、娃娃图,然而她们大多数却没有一个小孩的成绩斐然。这个小孩名字叫高荫章(1835—1906),字桐轩,五岁时,见到什么小动物都会模仿它们的姿态,用棍子在地上画出来,天长日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画得特像,十几岁时,他可以把几种动物放在一起组成一幅动物嬉戏图,有的憨厚,有的暴怒,有的嬉笑,有的怪诞,亦庄亦谐,甚是有趣,人们看了啧啧称奇,更让人们称奇的是他凭着坚韧的毅力无师自通。十五岁时,年画一上手,他的画风就与别人不同,无论是人物还是飞禽走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渐渐地他的年画有了声望,大家向他求画,他不吝啬笔墨,而富人让他画,能推脱则绝不应,推脱不了时用高价让其退避三舍。有一次,一个富家公子知道他画的年画出名,就为要他的画,不吝金钱,要多少给多少,桐轩只好应付他,给他画了一棵白菜和一只蝈蝈,那棵白菜就像地里长的,既水灵又嫩生,而绿里透白的大肚蝈蝈站在白菜上似乎用嘴梳理它的长须。这位少爷看了别提多高兴,扔给高师傅一个金锭,伸手准备摘画,天上立刻乌云翻滚,大风骤起,风卷门开,把画刮跑了。第二天早上,一位孤寡老人推开房门出来,老人低头拿锄头,发现锄头把上裹着一张纸,小心剥下来一看,年画上只有一颗白菜和一只蝈蝈,进屋便把它贴在墙上,那蝈蝈就像活的一样冲他叫,他太喜欢了,每天看它好几次,突然有一次发现蝈蝈不见了,在一棵菜的叶子底下找到了它。那一天,老人出门被雨水淋透了。老人发现每当蝈蝈藏在叶子下,准得刮风下雨,它成了天气预报。这件事被老百姓越传越神乎,结果传到慈禧耳朵里,把高桐轩召到宫内,成为御用画家。
十四、锄地的会作古诗词
在杨柳青,锄地老百姓叫镐地,把镐地的人叫摞镐把的,无论锄地还是摞镐把都特指农民(无贬义)。农民的特点就是日升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不停地在地里侍弄庄稼,农民们自嘲自己的工作叫“修理地球”。既然日升而作,日落而息,也就没有时间干别的,然而就有农民在“修理地球”的间隙作诗、作词、习绘画。诗者乃托物言志,就是把具像的东西抽象,大都是文学作家中的“极品人物”,只有他们能做到,它就像王冠上的那几颗珍珠一样极为宝贵。修理地球的人能与他们相比吗,显然不能。可在杨柳青就有一些农民不信这个邪,其中,已故的魏树今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他把自己的笔名起作“锄笠”,刻枚闲章的图案也是一顶草帽覆盖一把锄头。当看到他填的词时,你可能就不认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七十岁时,他与同学(解放初私塾)聚会,即兴填词:“光阴快,时刻分秒都不待,都不待,犹新记忆万般皆改。同乘旅客稀疏败,稀疏败,天留我等今康在,今康在,转眼之即年将半百。”词很贴题,句无华丽,朴实得让人联想起农民的性格。现如今社会浮夸,人心浮躁,崇尚攀比,看到这种现象,想到魏公一首填词:“天地始形成,享物天供。北蓄牛羊,南罕兔。莫比失平,大地本无公,山海丘平,公为均荡复均衡。缠比终归终有事,极必归终。”这首词虽难懂,却很朴实,表达了一个非常浅显的哲理,即所有人得到的,都是老天爷赐予的,只有老老实实享受这一切,没有公平不公平之说,如果非要攀比,终有一天你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说的全是老百姓的话,因此他特别受老百姓欢迎。
十五、马儿成了摆设
在六七十年代,马车是最普遍的运输工具,马儿也最金贵。杨柳青的哪个生产队有几匹顶强的马,那个生产社员劳动强度就轻一点,最靠力气的活儿像耕地、犁地、笆地,像轧场、往队里拉粮食(一般粮场与队里大概距离近者16余里地,远者40余里),如果没有马匹,这些都需人力所为,而人们下地也只好用腿,下过地的人都知道,趶呲(ku ci)趶呲好不容易走到地里,还有最重的体力活将等着人们去做。像挑水、点种,赶上抗旱保墒,从远处沟、壑里挑水浇地等,完全是“扁担炖肉”。看着别的街的马车载着欢笑从自己身边一晃而过时,那种又羡慕又嫉妒心理油然升起。嘴里不觉脱口而出“你看人家”。劳累一天还得用腿走回家,酸楚的腿像灌了铅,好不容易捱到路上,看着别的街的马车载着欢笑从自己身边一晃而过时,那心里不是羡慕也不是嫉妒,那是恨,恨队长没有本事。随着经济的发展,杨柳青七街逐步添置了手扶拖拉机、20拖拉机、55拖拉机,有了解放牌汽车,打了深水机井,露天沟渠变成暗渠,浇水也变成喷灌、滴灌,一片片桃树、梨树、苹果树、葡萄树。社员们不但摆脱了繁重的体力活,马儿也只干倒短儿的活儿。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一点也没错,农业在于机械化、水利化,实现了这两化目的是让社员们摆脱贫困,摆脱繁重的体力活,这是多么英明伟大啊。马儿本来是替人们干繁重活儿的,由于介入了机械它也被解放出来了,除了倒短儿,就成了摆设。说白了就是显摆,可不是穷显摆,就说三大套,三匹马,一水儿的大红色,红鬃被整理得整体划一,新鞅銬,红色褍铃,走起路来叮当悦耳,再看把式,高高个儿,青色裤褂,脚蹬青靸鞋,内套白袜,手握长长的皮鞭,系红缨头,往空中一甩,啪的一声,看上去那才叫飒利一棵杆儿,精神。走在路上,马儿雄赳赳,气昂昂,见着人,把式老远就“驾驾”喊个不停,生怕别人看不见。干活时,他换上干活衣裳,舍不得马儿,他自己扛,一旁的马儿望着他“灰灰”叫着,意思说我身肥体壮,我干那些如小菜儿。他拍了拍马儿的头,宝贝儿,我舍不得你啊。马儿把头依偎在他的手上来回摩擦。
作者:徐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