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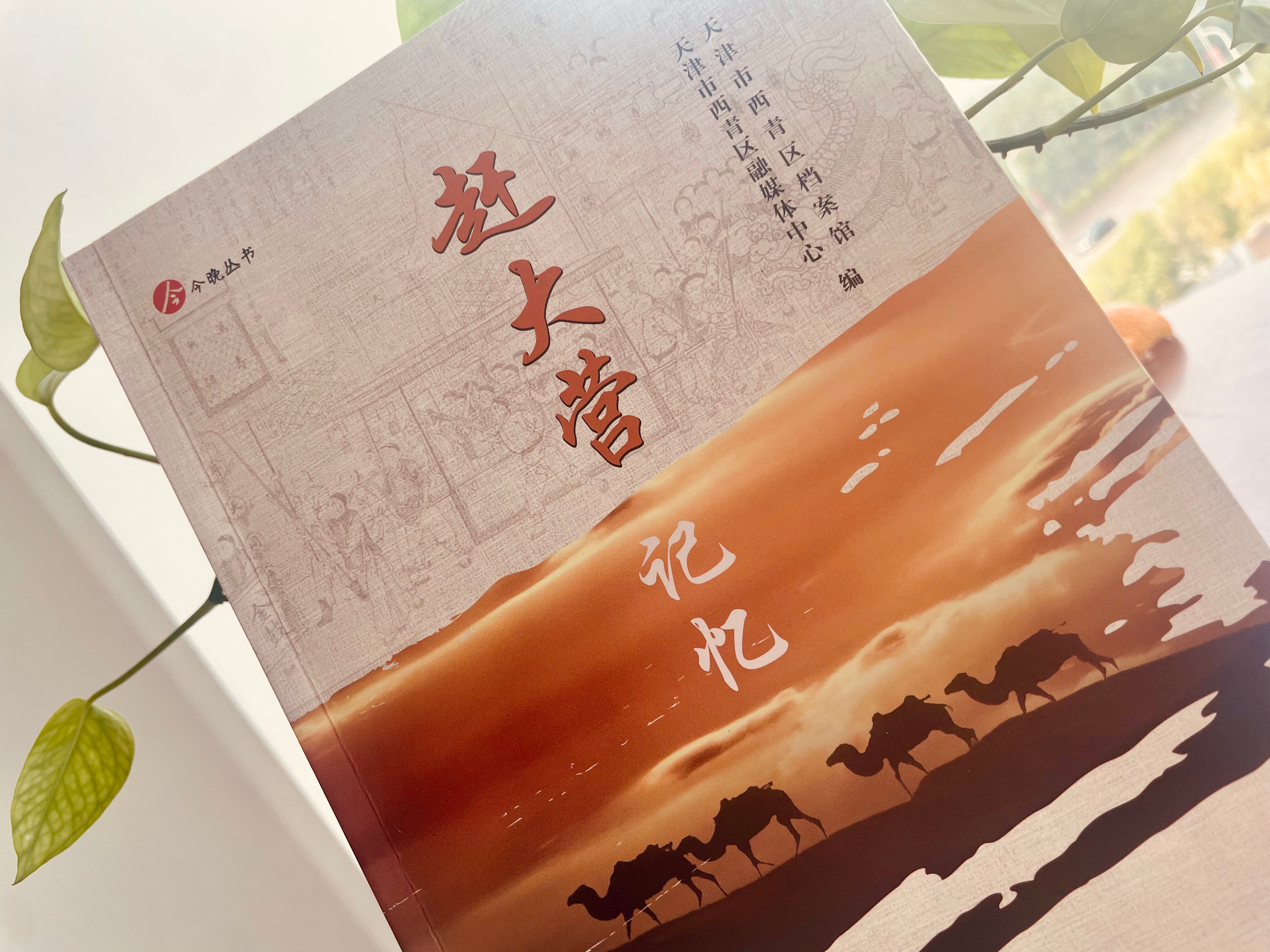
温世霖是天津宜兴埠人,曾创办北方最早的女学堂,为同盟会重要成员。近代首场学运宣统二年(1910)在津爆发,温世霖作为领袖被朝廷发送新疆。入民国后,他因不满军阀政治,壮年愤而退出政界,故少为人知。留下的《昆仑旅行日记》也束之高阁。笔者在编注此书时,发现其内容堪称“综合考察”记录,有关天津商帮的史料多达一两万字,是近代天津经济辐射大西北可贵的历史见证。
茅盾《新疆风土杂忆》说“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到新省,实为左宗棠西征[按始于光绪元年(1875)]时随军的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2000年,天津市有关方面曾组织实地调研,《今晚报》有大量报道,参与记者得知《日记》内容后,称原先一直苦于缺乏文献印证。
温世霖漫长旅行的花费,除官方承担外,全靠各地津商“自动发起向五省同乡募捐”,更多的被温世霖辞谢。从西安开始,沿途大小城镇多有津商分布,荒僻城镇也不例外,例如甘肃境内的平番县随西征军的后勤供应而兴衰,当时也有津人经营的洋行。新疆“通商大埠”古城(今奇台)可作典型。《日记》说:“凡同乡商号之名望较崇、资本较厚者约二十余家,其领袖均到会欢迎。”
天津人的经营覆盖各行各业,从《日记》中随处可见的京货店到经营出口的洋行、收购单项土产的商号;还扩展到典当、烧锅、酱园等行业。津商还对重要行业形成垄断,例如作为新疆最宝贵资源的玉业。温世霖在西安出席古玩业主的招待,同席有四人都是专门为北京前门各珠宝店代理收购的津商。春茂和杨济卿家获得和阗(今和田)“玉石第一家采掘之权”。
各地津商都有会馆作活动中心,也有商会等新式社团。在新疆奇台,《日记》记载的三家商号老板“皆该地商界之领袖”。在兰州,津商云倬樵(温世霖的表弟)“现任甘肃商会副会长”。
津商在西北的支配地位,突出表现在与山西、陕西商帮的对比上。清代晋商曾称雄于全国,大商埠无不建有壮观的山西会馆,但在西北,不及津帮。
一般认为天津人故土难离,四海经商远不如山西人。《日记》记述,某镇有古晋会馆,但西征带来的繁荣过后,“铺面房屋空闲者甚多。”津商的繁盛何以更为持久?答案显然是天津有海港作为大宗进出口贸易的依托,内陆的山西无法企及。
津商的后代在当地扎根,跻身于新疆社会中上层,任职于邮政局、官钱局(银行),有的成为地区行政长官,例如哈密厅监督。官位最高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也是直隶乡亲。新疆教育界的人才几乎都来自天津,例如主管全省学务的提学使、省视学(督导各地学校),都是杨柳青人;迪化(今乌鲁木齐)学务公所科长是“天津西沽大学优等毕业生,科学造诣精深”;陕西高等学堂德文教习、英文教习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
放大分析研究的时空尺度,可以得到结论:近代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由天津带动的。这与当代天津战略地位的确定紧密相关,值得进行专题研究。
作者:高成鸢